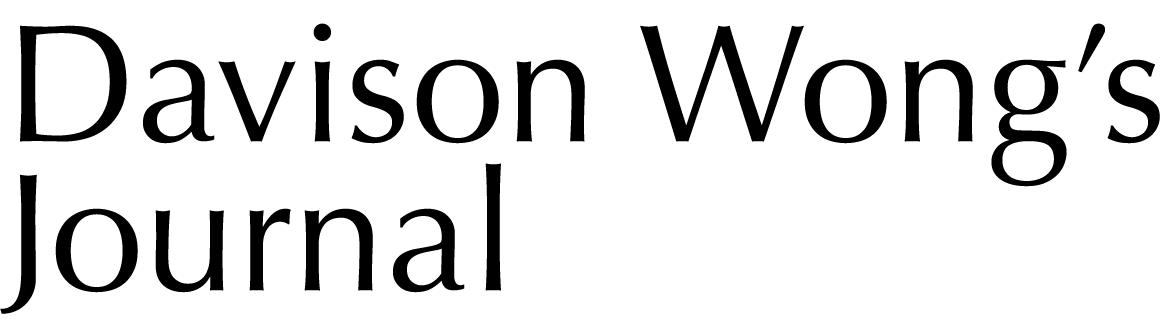CONTENT
【時代恨愛,心中激盪——喜利唱片與韋生的水邊故事】
1985年2月15日不是甚麼特別日子。但對譚詠麟與喜利唱片的韋生來說,這天正是他們人生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捩點——憑著這天發行的專輯《愛情陷阱》,譚詠麟登上了個人事業的高峰,從此紅遍全香港;而當時不過十來歲的韋生,亦在這天第一次涉足家人「喜利唱片」的生意,正式加入唱片行業。
三十六年過去。譚詠麟成為落後與守舊的同義詞,唱片業由盛轉衰,一度被嫌棄的黑膠則再受追捧。至於韋生,萌生過退場的念頭,曾經停售唱片,最後還是在街坊的鼓勵下,重拾初心。時代流轉,這刻還在夕陽城市守住夕陽行業。韋生對唱片與此城的感情,又如何能在一時三刻說清?
由沙灘炸機說起 唱片業的輪流轉
「賣唱片,係因為鍾意聽歌。落到舖頭幫手,聽乜歌都得嘛。」韋生入行時的八十年代,經濟剛剛起飛,社會無太多娛樂,大部分人的嗜好都是聽歌,「當年唱片還是以Cassette帶或黑膠為主,我哋會托住部好大嘅Cassette 機到沙灘,勁大聲播歌,俗稱『炸機』。」人人聽歌聽到痴狂忘形,〈愛情陷阱〉或者〈無心睡眠〉等於潮流指標。「當年歌迷,買碟習慣係買一隻聽,再買多隻留念。所以一線歌手嘅碟,我哋一間舖都賣到千幾二千隻。放到業界標準睇,一白金銷量,即係賣過五萬張,完全唔成問題。」
踏入九十年代,唱片的主要載體亦從Cassette帶與黑膠轉為CD。「比起聽黑膠會聽到啲『嘞嘞聲』,CD音質當然好好多,但缺點就係成本貴。」CD、DVD成為主流,但淡出時代舞台的速度也令人反應不及。「估唔到而家又興返聽黑膠。」面對科技與網絡浪潮,唱片行業的衰落始終是既定現實。韋生無奈笑嘆,「而家買碟,不過好似買返件心頭好玩具。」
拎個心出嚟做 總會有人欣賞
常言道:「愈難的牌,愈要俾心機打。」無論打牌做人、創作音樂還是繼續賣碟,迎著劣勢,守住初衷,也許總能渡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。近年唱片界偶然都會有幾張備受期待的唱片做救市良藥。「2018年有張敬軒嘅《Senses Inherited》,當然唔少得麥浚龍同謝安琪嘅《The album》系列、最近Mirror新碟《One and All》。歌迷預早打電話訂,嚟到都係冇貨。我都唔好意思成日令客人失望。」
現在做唱片僅求回本,唱片公司幫時令的歌手出新碟,往往賣完一版就不再加製。像去年尾受追捧的許廷鏗,專輯《Negative》一推出便火速斷市,市面不乏三、四百的標價貨。韋生笑言,「貨量少,就有人炒。」喜利沒有跟住炒價的潮流,自然是將心比心,不希望在仍買實體碟的樂迷身上佔便宜。
離散日常 有誰共鳴
賣了唱片三十幾年,韋生已跟街坊打成一片,老闆客人不分你我,在唱片舖談盡天南地北。「近嚟大家講得最多,都係呢個歌手變成咁,嗰個歌手點解會咁樣做。」時代變,人情變,昔日受盡敬重崇拜的巨星,拋棄了令他們名成利就的支持者,對城市的荒誕沉淪好像都視若無睹。韋生不無慨嘆,但仍寄語勉勵街坊,「繼續喺度生活,做好自己係最緊要。」
最近移民再成熱話,你我身邊總有出走他方的親友舊識。當離散變得日常,憂傷痛苦無法訴說排解,流行文化如廣東歌,就是難得的情緒出口。訪問尾聲,韋生推介Rubberband的最新唱片《i》,託付他自己、也是大家的心聲:「我諗你聽落去,就會搵到有共鳴嘅嘢。」
鳴謝: 喜利唱片
文字:餅 @水邊故事
社區需要唱片舖? 喜利唱片韋生:「同街坊嘅感情好難得」
PRODUCED FOR
Shui Pin Stories, Samuel Lai Kwok-wing of Yuen Long District Council
元朗區議會黎國泳辦事處「水邊故事」
MY POSITION
Directory Of Photography, Editor